![图片[1]-(9794期)全新短剧玩法3.0,轻松日入1000+,私域零成本操作,全程干货-飓风网创资源站](http://yz03.cn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4/57386fbb8120240406212538.jpg)
短剧推广那么火,为什么你却不能分一杯羹,赚到这份钱?短剧其实就是爽文小说演化而来,情节紧凑,主打看的过瘾上头,虽然剧情俗套,但是架不住有人爱看,刚开始做短剧的一波人确实赚到钱了。那么做短剧推广,账号没流量,其实不是你的能力不行,而是现在大环境太卷了,无数的人都在做短剧,内卷严重,客户群体就这么多,之前短剧的玩法一直是挂载小程序,粉丝进去小程序之后,在里面付费冲会员后才能继续看,而且你作品上挂载小程序,就跟你在作品上挂载商品一样,会被官方限流 今天华哥就教大家一种新玩法,避免内卷: 那么新的玩法就是我们从公域平台引流,最后在私域变现。在私域把这些短剧合集打包出售给客户,对于在小程序冲会员,价格更便宜,而且得到的短剧资源也多得多。


![图片[2]-(9794期)全新短剧玩法3.0,轻松日入1000+,私域零成本操作,全程干货-飓风网创资源站](http://yz03.cn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4/12c7d9424720240406212538.jpg)
© 版权声明
THE END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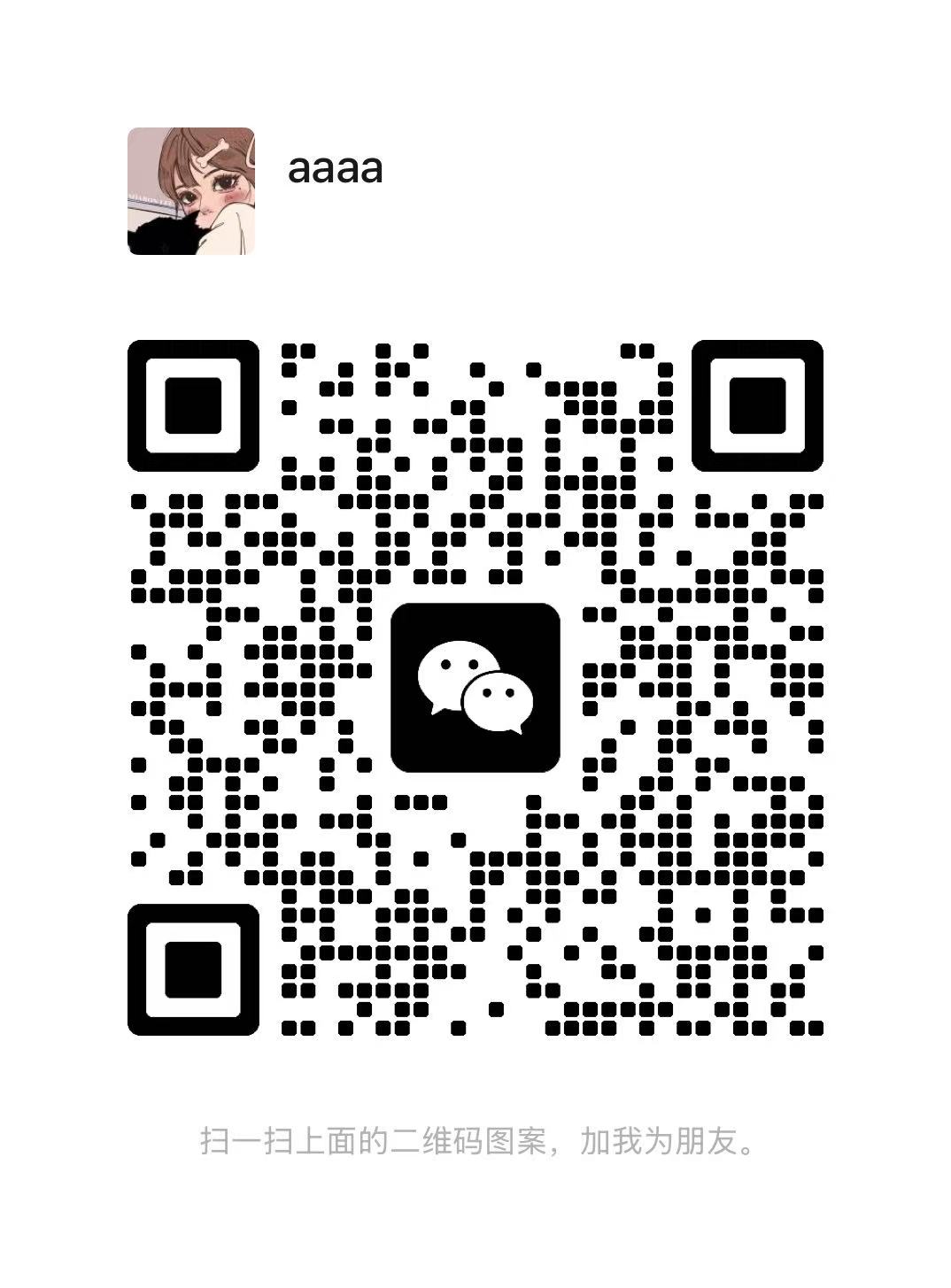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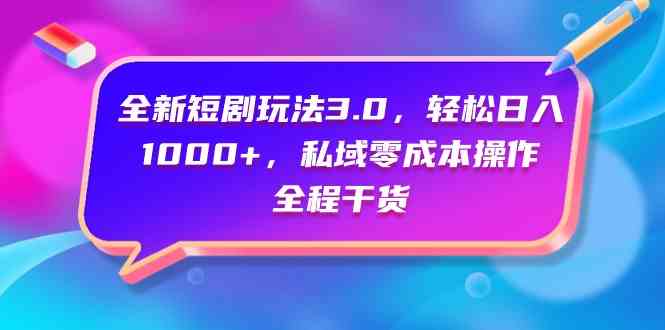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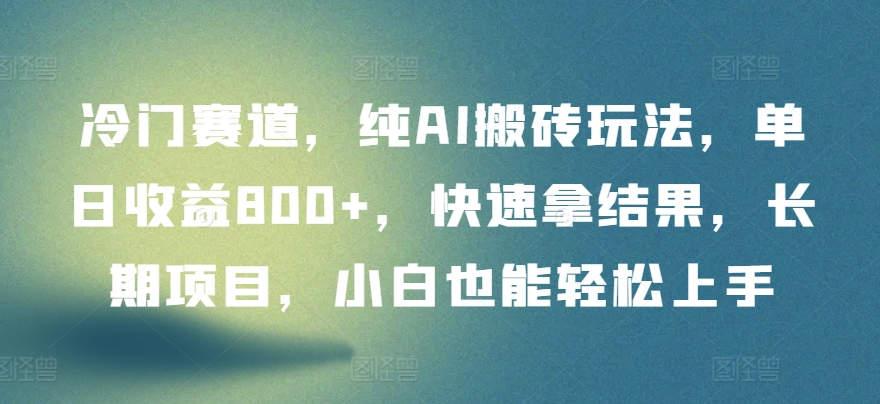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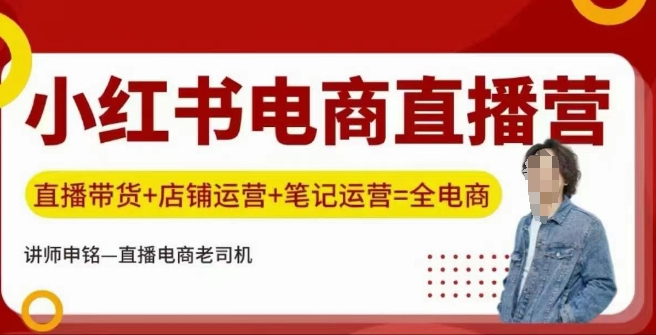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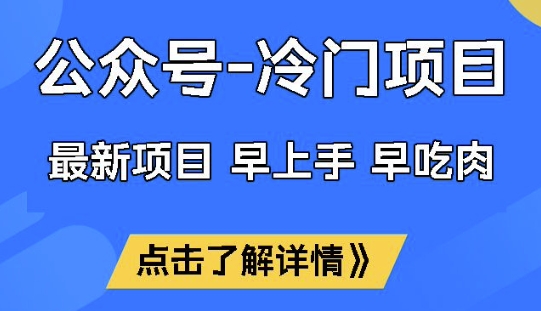
暂无评论内容